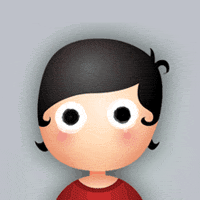汪天钊丨三十三层楼盘下的回响
他曾是一个农民,修过11年高速公路,7年前到洛阳定居,他爱文学、爱写作,他写他原汁原味的生活!
他的文字像山间野草,新鲜,生猛,充满人性温情。
在那么黑暗、潮湿、嘈杂、脏乱的环境里,他居然觉得幸福!
为什么?也许,你能在他的文字里找到答案!
他叫汪天钊,作品散见《散文选刊》《奔流》《牡丹》等多种文学期刊,多次获奖。他的《天降的修行者》入选《2016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春天农事》获河南首届奔流文学奖散文奖。
即日起,我们每天推送一篇汪天钊的散文,一起欣赏。
汪天钊的散文都很长。本想把它们拆拆解解,弄得短短的给大家看,但是犹豫来犹豫去,觉得还是原汁原味地呈现比较好。需要静下心来欣赏,看完感觉如何,请在文末留言,小编会反馈给作者喔~
为了缓解大家长时间盯着屏幕的不适感,小编配一些绿色的图画。
我所居住的这所城市和所有城市一样,楼盘就象春笋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生长速度比庄稼拔节都要快;并暗暗地憋足了劲头儿比试,你高,我比你更高,你恢弘,我比你更恢弘,你富丽堂皇,我比你更富丽堂皇,今天是潮流的主导者,明天或许就成了陪衬者;它们试图把各自所独有的优势和姿色无限地渲染夸张,诱惑着人们,让你走进它,什么样的结果也没有俘获你重要。
一
这是一处三十三层楼盘的地下室。我的工作是看场子,所属电力施工队,电力设备都很贵重,技术含金量高,电缆、电柜、变压器等等的材料主要是铜,防止盗窃,也防止破坏。
施工当中的地下室里的空气不流通,氧气稀薄,严重污浊。刚进去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耳朵似乎被堵死了,伴有压迫感,头很闷,思维就象锈死了的螺丝钉,用了很大的劲儿拧只是吱咛了一下就戛然而止,傻子一般。建筑垃圾随处可见,建筑材料随处堆放,最后清理时用汽车往外拉,不知道拉了多少车。地上灰层很厚,灰尘极其细腻、轻扬、有流动性,任何一种动静就能惹得它们飞扬跋扈;捏着脚步轻轻地走进去再走出来,鞋子和裤脚上就是一层,跺跺脚,一部分腾云驾雾,一部分钻在缝隙里钻得更深。拉着一根钢筋走过去,就是一道升腾的白烟儿。床铺每天起床后都要卷起来,或者用纸板盖上,到了晚上用手指头一划都能看出灰层的厚度。钻孔、打墙的粉尘间隔一段时间总要给空气增加一点重量,汽车进来就是在制造一场弥天大雾;好在地下室里从来不刮风,否则单单灰尘就能把人呛死。地下室没有厕所,厕所却无处不在,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厕所,每次都去了那里,一些时间过去,一个偌大的房间里都是一个人的杰作,一堆一堆地摆得分明。其实这都可以忽略,墙体涂料一直都在慢慢释放着气体,或浓或淡,嗅到或嗅不到;一些管道就在现场做防腐处理,刺鼻的气味时常飘散开来;现在人们都不再孤陋寡闻,谁都知道那是甲醛,甲醛是一种致病的恶魔。
地下室是蚊子的天堂。盛夏时黑压压地,照明用的是“千瓦棒”,千瓦棒发出巨大的热能,冷了能用来取暖;昆虫都有向光性,蚊子纷纷扑向千瓦棒,只听噼噼啪啪地一声响,蚊子被烧死纷纷落地,千瓦棒无意之间充当了灭蚊的武器,它的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蚊子尸体。蚊子繁殖得快不是没有理由的,它们如此地被杀死,不然还不断子绝孙,千瓦棒终没能打败蚊子,蚊子依然前赴后继。蚊帐在这里也不免尴尬极了,不管孔径大小,蚊子总是能突破防线。到了冬天这里就成了蚊子最后的营地,虽然大部分的已经销声匿迹,总有一小撮在负隅顽抗,轮番出来觅食。我是一个惧怕蚊子的人,蚊子的毒在我身上似乎有着更大的威力,奇痒难忍,很多时我气急败坏地拍打在我脸上叮咬的蚊子,蚊子没打着,自己的脸倒是火辣辣地疼。蚊香很有效,虽然空间很大,不能杀死,但能驱赶;夜晚睡觉时陪伴我的就是一盘点燃的蚊香,从夏天一直持续到冬天农历十一月底,事实上十一月底蚊子也不绝迹,仍有一两个在耳边哼咛。
但让我远没有料到,因为楼盘迟迟不付工程款,施工方没有办法,使用了看似无赖却又最实用的办法:你不给我钱我就是不给你送电,就这样一直拖着,不知道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到了最后所有施工人员都撤掉之后,整个地下室只我一个人,寂静得近乎恐怖,我终于读懂了孤独的含义;我对蚊子竟然少了原来的咬牙切齿的憎恨,只有它们才不肯舍我而去,我听出了它们声音的美妙,那样从容和自我;我无意间成了是它们唯一的欣赏者。
地下室原本就潮湿,冷飕飕的。不知道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排水沟总是满满的,然后向外溢泻扩张,隔一段时间就要抽水,不几天又满了。出口处和东边的地下室大面积积水,一片汪洋。人们在水里建立了一条路,就地取材,各种材料都有:泡沫、砖头、竹笆、竹胶板、方木,这些东西都被浸泡着,有的被埋没。人们在这样的路上掂着脚尖,蹦跳,扭转,极力地掌握着平衡;稍不小心一趟儿没走到头鞋子就湿了。上个月秋雨连绵,一连下了一个礼拜。雨水从入口处进来,水漫金山,水成半圆状向我们这边包围了过来,电力设备却偏偏怕水,必须要堵水,唯一的材料就是沙,我用翻斗车偷了砌墙施工队的沙子,筑起一道屏障。沙子是透水性的,只是暂时的,水很快透过沙子继续向前逼近。我用铁锨泼水,泼完之后继续渗水,继续泼,我和老天在打一场没有预期的战争。
潮湿是运动系统的大敌,在地下室里待久了膝盖脚趾都是冰凉的,走出去的一瞬间全身都是温暖的,但冰凉在骨缝里尤为清晰;每天早上起来,觉得关节和腰部都是强直的。看场子是两个人,另一位是老者,我喊他“老哥”。这位老哥是施工队里的老成员了,他有严重的腰疼病,就是疼得干不成活儿,才安排他看场子的。每天早晨起床他就像拉开的弓,屁股趔趄着,一手撑着腰,裂着嘴活动了好大一阵子才慢慢地直立起来。他已经六十岁了,还有高血压,前几天他犯病了,买了一袋子的药。他其实很让人羡慕,他一双儿女都是大学生,闺女毕业之后在省城人民医院上班,也买了房子,儿子也早毕业了。但儿子的事情让他常常夜不能寐,他儿子属于北漂族,在北京拼打了多年还没找到一份稳定工作,望房兴叹,婚事八字还没一撇;他儿子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了。他经常在地下室里来来回回地走动,脚步声嚓嚓地响,我不知道地下室里的脚印儿有多少是属于他的,他在地下室里走了多远的路途,假如单行地延伸出去,一定是遥远的。但我从没有听到他抱怨过,或愤怒,看到他大多时只是默默地吸烟,在昏暗的光线里如萤火一样忽明忽暗,希望是一个多么缥缈虚无的词儿,我常常疑惑此时变得生动而具体。
通电的电缆线都在地上,被车辆碾来碾去,和很多尖利或坚硬的东西有过亲密的接触,现在又都在水里浸泡着。其实,谁都知道安全的重要性,但在事实操作中确实不易,不可能整日地念着安全条例施工,更不可能整日地拿着劳动协议干活儿,真的这样整个社会都无法运转,所有的活动休矣。谁都不怨,怨的话只有怨老天,怨老天也没用,因为大多时候总是很安全的,一旦发生在某个人的身上,只有怨自己的命不好。我族家的一个哥只有一个儿子,二十多岁时就是在地下室里被电死的,因为电缆线在水里漏电。这位哥当时近五十岁,妻子也做了绝育,儿子只给他们撇下两个幼小的孙女。再看到他们夫妻二人让人不敢相信,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极度虚弱憔悴,完全变了面相,似乎是患了绝症的病人,他们两个本是开朗的人,现在沉默寡言,在人们视野里也很少出现;谁都会解劝人,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头上他都知道:任何的劝解都是无效的,怎样的胸怀都是无法承受的,再高的境界都是不堪一击的,什么样的钥匙再也打不开这样的死结。
还好,这里什么意外都没发生。
二
才进来为了熟悉环境我在地下室转悠了几次,之后就很少大范围地走动,生活依然在方寸之间。我每天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通风口下,通风口下有信号,虽然信号时强时弱,或者中断,但那是我和世界联系的窗口,证明我还没有被遗忘;我不断地刷屏,渴望有朋友给我发消息,或者我给朋友发消息,但我也不想让他们来打扰我,我去打扰谁。很快我就发现,这种意义远远比不上蓝天白云、空气、以及光明,我站那里久久伫立,久久地仰望它们。我做深呼吸,我感觉到了清新的空气盘旋着下来,轻盈能从脚底下升腾起来。我觉得我在光线的照耀下就是一个即将吐丝的蚕,浑身透亮,任何一种隐秘都无处躲藏。在中午我不肯错过,若是晴天,一定有阳光洒落下来,我用身体静静地接着它,阳光从所未有地温暖和明媚。我还是相当浮躁的,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根本没有看到从通风口爬进来的四五条青藤,它们很长了,绝对是在我来之前就爬进来的。那天我站在通风口下傻傻地站了半天才发现它们,发现之后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没有想到我会感动,随着岁月的磨砺,我认定我早已坚硬如铁,冷峻如霜,小资再也无法撼动我,而这几条青藤却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柔软,似乎就是为我而爬进来的,在等待着我的到来,一直在向我打着招呼,当我的目光和它们相遇的一瞬间,我的内心禁不住真的湿润了。
我还可以走出地下室,站在入口处看车水马龙,人们来来往往;夜晚街灯璀璨,不远处的广场舞如约而至。最自由时就是吃饭时间,我们两个人轮换着上街吃饭,可以顺便在大街上溜达,进超市购买日常用品,却也不能太任性,就是一个人在地下室里24小时值班,也不是另一个人长时间离开的理由。总觉得这样的自由太短暂,太心慌意乱,就像鱼儿浮出水面冒了一下泡,就这样的一个泡,让我感觉到世界是从所未有的美好,很多堵心的事悄然溜走了,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放下。
我从没有想到我能过上如此理想、如此安逸的生活——只要我不离开现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一面可以挣钱养家糊口,一面还可以写文字;平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实属浪费,我一点一点被掏空之后再坐下来就是憋的,憋也憋不出来,就象拉痢疾。一张用两个砌墙的大砖支起了一块竹胶板,一把能随身携带的折叠椅子,一盏直接插在插座上的节能灯泡,一台旧了的手提电脑便是我的全部;当我像点豆子一样敲击键盘时,过往的人们总是要扭头看我,虽然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但我知道那表情一定是异样的,我已无所谓。
我是多么卑微,比尘埃还要卑微,又是多么高傲,比王还要高傲。我极力想逃脱这种生活,我真的感谢这种生活。
我们家乡有句老话:“上一半下一半”,说的是盖房子,意思是房子的主体已经完成,只是工作量的一半,剩下的事情虽然小,似乎很不起眼,但很繁琐,也占工作量的一半。高层楼房其实也是上一半下一半,楼房是一半,何况大面积的装修由购买者自己负责,装修是无穷尽的,有多少钱都能扔进去,仍然是上一半下一半;每一层的结构就是再复杂,从一楼到顶层是一样的,把一层研究清楚了,以后的每一层不过是复制而已。下一半是地下室,水电、消防、通风等主要设备都集中在地下室,车库只是一种副产品,空间的合理利用而已。楼盘早已开盘,购买者可能早就入住,但地下室的施工远远没有结束。
我总觉得楼盘设计人员的脑子是诡秘的,是那样地精准和严谨,所有的空间都逃脱不了的他们的掌控,每种系统、每个构造、旮旮旯旯都了然于胸,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繁而有序,杂而规整,他们经营的是建筑,也是艺术,恢弘、靓丽、震撼——地下室密集着各种管道,各种管道纵横交错,互不干涉,高度、位置、走向,在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都要正确无误;在这里没有想当然,我一看见它们我就开始怀疑我是否还有智力。不过这是他们份内的事,他们就是靠脑子吃饭的,要把它们体现出来,具体的操作却是和身份毫不相称的民工,他们当中总有人能胜任这一职务,就是一个普通的民工,对本业务也要非常熟练,否则是不受欢迎的,一个施工队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施工队,老板的效益就会打上很大的折扣。
看不出他是一个技术负责人,个子粗矮,似乎比武大郎高不了多少,脸就象烤焦的锅盔,嗓音粗憨;他和其他的人员一样地干活儿,一会儿抬架子,一会儿上架子上打洞,一会儿抬管子。图纸很大,象地图,他把施工图纸摊在地上,象即将打仗的将军一样蹲在地上仔细审查图纸,然后又观察现场,最后告诉管子的准确长度,打洞的具体位置,需要几个直接头、弯接头、比划着支架做成什么样子。
巾帼不让须眉,但在建筑工地里看到女人出现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虽然她们不是主角儿,大都是“帮手”,却如一只凤凰和一大群狼站在一起,芝麻掺进了豆子里,很不协调。她们每天和男民工一样上班下班,一天到晚忙碌。我和她们从未交谈过,她们的一切我都是未知,但我知道她们的内心绝对是非常强大的,火热而又极其淡定,她们不需要任何人怜悯,怜悯是无助的,也是虚假的。我经常看到的是砌墙施工队里的一个女人,三十多岁,眉目清秀,说话很好听。她打扮得像一个厨师,穿着做饭的用的大围裙,几乎能拖到地上,戴着迷彩帽子。看来她是“老小工”了,听不到有人吩咐,她兀自向搅拌机里填沙、倒水泥、倒水,然后提灰、搬砖。
随着设备陆续地安装在了配电室,晚上就增派人员,配电室多少不等,这个楼盘有七个配电室,一个人看管一个配电室,最后晚上增加到七个人。成员自然是施工队里的成员,白天干活儿晚上看场子;老板有几个工地,他们经常在几个工地之间来回奔波,回来时往往三更半夜。由于机动性,他们的床铺更加简单,就一张用过的竹胶板,来了一铺就睡,天明了往腋下一夹就走。看一晚上20元,也算是额外收入,快够每天的伙食费了;施工队不管饭,都是买着吃,各吃各的。民工都是体力活儿,吃的都是大份儿,日子不可长算,吃什么他们都是合计着来的,喝牛肉汤喝最便宜的,5块的,烧饼吃了几个。
其中一个老头人们都喊他“老赵”,绰号叫“烧饼就大葱”。老赵的一分钱掉在地上能摸场一片大,不知道他本来吸烟不吸烟、喝酒不喝酒,但在工地上他从来喝酒不吸烟;看工地民工都要买蚊香,他从来没买过,睡觉用被单子把整个人都裹住。问他能睡着不,他说那你还是不瞌睡!他吃饭啥便宜吃啥,能填饱肚子都行,他经常吃烧饼,就的是大葱,喝的是自来水;有一次中午电力公司的领导到工地现场看到了,这位领导在开会时点名道姓地批评了施工队的老板,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员工啊!老板本来不信,下来一打听果真有此事,是老赵,他训斥了老赵一顿:以后不准吃烧饼就大葱,再发现一次滚蛋!老赵连连说,不吃了,再也不吃了!就是在那一次,老赵声名远扬,烧饼就大葱就贴在了他的身上。
放电缆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电缆碗口一样粗,弹性韧性十足,死猪在它面前屁都不屁,想要制服它必须要拿出骨髓里的真劲头儿;电缆需要“抖劲儿”,把电缆从电缆盘上拉下来盘成8字形,还不能盘成反劲儿,乱绳子难解,电缆绳一旦盘乱,就是严重的错误,什么都耽搁了;每通过拐弯抹角处就是一场艰难的考试,虽然考题很简单,做了无数次。放电缆的民工没有年轻人,基本都在45岁以上,有几个都在60岁左右,这几个老头却是施工队的骨干,见证了本施工队的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有个老头说他们50后这一茬人上来就是唱老旦的,没欢脆过一天:经受过致命的饥饿,以前的农活儿基本上都是靠体力完成的,现在出来打工拼的还是身体。
但工地上的民工谁也没有像老赵那样豪爽过,老赵的儿子本来就是大学生,在大学里又入伍,因为刻苦优秀,被选拔到北京某军事院校深造,工地上的人们说这是喜上加喜,还不庆贺?民工向来没有多少正经话儿,都是开玩笑的,没想到老赵是认真的,他当即买了两条玉溪烟,花了几百块,人人有份儿。其实干活儿谁也没有老赵忒实在,放电缆每次盘8字时人们都异口同声说:老赵上!老赵从不推辞,由他主导盘的8字很少出错。
三
地下室似乎就是一个巨型的耳机或者是大鼓,它能把最微弱的声音尽可能地放大,放大到极限,声音在这里也犹如寻到了适合它生存的最佳条件,它没有理由不竭力发挥到最大能量,产生最佳效应。任何一种声音都是宏大的、震撼的、飘渺的、颤抖的,袅绕的;沉闷而又空灵,虚无而又真切,绵软而又锐利;都在展示着四两拔千斤的力量。翻斗车的咣当咣当,就能演绎成一列火车的飞奔;水钻钻墙孔,就可以膨胀为飞机起降的嘶鸣;敲打灰桶,就能轻松地渲染成夏天里雷电的咆哮;外面挖掘机破碎路面的嗒嗒声仅仅通过地下室口传送进来就成了汹涌的潮水,惊涛拍岸,整个地下室都在地动山摇。切割的声音、钻孔的声音、砸东西的声音看谁能超过谁。摩托车,面包车、机动三轮车、自制的拖拉机铲车、搅拌机的声音远远比万马奔腾,或者肆虐风暴都强劲。
送风筒和桥架其实就是用铁皮做的,一节一节组合起来,用量很大。隔了一些时日就要送进来,卸车时落地的声音、相撞的声音、和车帮的磕碰声,每一环节都不甘沉默。在很多声音同时响起来的时候,它以绝对优势独占鳌头。如果拖着一节通风箱或桥架走过去,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同一种声响,近距离远距离,隔着墙体不隔着墙体,在头顶上或在本层,听起来都具有各自的属性。比如电钻,在头顶炸裂,在附近震动,在远处轰鸣,隔着多层的墙体,似乎风在呼啸。每种物体都掷地有声,不管是钢管、铁架子、还是锤子、钎子、漆桶、砖头落地都要发出一声属于自己的声响。每种声响变化莫测,可以捶打,可以撕裂,可以刺入,可以淹没,可以捆绑,然后慢慢地收紧,可以用内力,不伤皮肉,却伤内脏,可以选择,什么都不伤,就伤你的神经,或者思维;它能精准地知道你的弱点,你惧怕什么,它就以什么来伤害你。白天就这样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响,要么独奏,要么合唱,你方唱罢他登场,这些声响把地下室憋得憋饱憋饱的,我怀疑几十层楼房的坚挺都是由这些声音支撑起来的。
夜晚,民工的小便声,就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在从容地敲打着屋顶。走动的脚步,是风吹过树林,也是侦探电影里的配音,沙沙的声音那样轻飘、那样清晰、那样让人警惕。说话声似乎从遥远的山谷传来,一句话也听不清楚,已经失去了话语的特征。如果有民工加班,响声和白天迥然不同,增添了八度的疯狂;他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们不知道,有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时间久了,当我走出去再听到地面上的声音似乎都很微弱,没有足够的底气;我说话无形之中腔调也大起来,我怕别人听不到。
光线的昏暗给眼睛带来了倦怠,它不想走动,就是走动也要借助于灯光,也仅限于灯光的范围,民工们干活儿时都要带着手灯、头灯、排灯、千瓦棒等等意想不到的照明工具。地下室似乎是枪战游戏里的迷宫,在门口处看到一个个人进来,进来之后就不知道他们散落在了哪里,一个人用目光去跟踪他们绝对是不可思议的;然而用我的耳朵则是一件相当轻松的事,只要我愿意,我完全可以躺在床上就几乎能判断出整个地下室里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都是谁,来自哪里,后来有去了哪里,但我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在干什么,有人没有,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结束。有的声音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可能已经完工,也可能原先的民工已经走掉,新来的还没有到来——民工来来去去,有些面孔熟识,大多陌生,熟识的也不知道是熟识,走掉根本不知道他们走掉,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们来到,如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们彼此没有记忆,淡忘无从说起。
有时间也能听到有优美动听的乐声,音质在地面上望尘莫及,属于真正的立体声,如临其境,似乎是给一个人演出的专场。一个上午熟悉的戏曲传来,我寻声而去,是在最远一个配电室里发出的,我看到在一个墙角处,放着一个常见的红放器,半个砖头大。一个民工正在里面批墙,批的是墙根儿,他是个胖子,胖子都难以蹲下,他竟然坐在了地上,他身上粘着杂乱无章的白色腻子,灰头灰脑的,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停顿,依然批他的墙,旁若无人。
有天早晨我还在熟睡时被流行音乐惊醒,音箱播放的那种,就在身边,可我没有听到附近有动静,我起身又仔细地看了一个遍,仍然没发现人的影子;我诧异起来,起床后我才发现声音是附近头顶上一个送风口里发出来的,送风口此时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音箱,歌声有一种和平常不一样的韵味,渗透着说不出的纯熟甜润,似乎经过了发酵;然而在送风口附近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动静,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神奇不已,我继续寻找,终于在很远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来源,原来是一个小伙子趴在送风筒上,正在安装送风筒,他的手机正在播放音乐。
我不想说他们本身之外一些空泛的话题,比如城市建设,时代潮流,或者他们的思想境界、人生态度,其实他们从没有给自己定过位,从也不会那样想;我只想说的是:他们在按照一种最为常态、最为本真的方式实实在在地生活着,纯朴而简单,这是他们生存的初衷;因为他们这样的常态和本真,才营造了一个常态和本真的世界,也正是这样的常态和本真,才是一个人生活下去的理由、维系天下芸芸众生繁衍生息下去的理由。
祝福他们,其实也在祝福我自己。
本文发表于2017《奔流》第四期散文栏目头题。
奔流文学奖由河南《时代报告》杂志社、《奔流》编辑部于2015年10月设立,共设5个奖项:中短篇小说奖、散文奖、诗歌奖、报告文学奖及新秀奖。首届奔流文学奖评选范围是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奔流》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其中散文奖共有3篇作品获奖。
配图均来自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