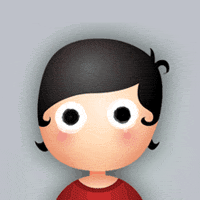尤迪特•海尔曼:用细节重塑一个新德国
印象中的德语作家,他们背负了太多历史和民族的东西。他们很复杂,人和作品一样丰富耐读。而德语这门语言,又让这种复杂脉络清晰。像写《铁皮鼓》的君特·格拉斯,肩上担着的是前成员沉甸甸的忏悔;像写《魔山》的托马斯·曼,,身上的乡愁也余音袅袅,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
德国作家可能没有俄罗斯作家的广阔和深刻,西西伯利亚大草原一望无际的风和雪,毛毯般大的雪片扑头盖脸砸来,寒冷入木三分冻地三尺。但他们绝对够复杂够沉重,是嗓音低沉克制理性的复杂和沉重,是条理清晰的四格变位。
然而,尤迪特·海尔曼还是不一样。她和和托马斯·曼不一样,君特·格拉斯不一样,和任何一个我读过的德语作家都不一样。她更像是一个法语作家。她不背负历史的民族的东西,她只负责人,她只负责生活。
尤迪特·海尔曼,这个德国女作家,1970年生于柏林。她成名前当过酒吧服务生,在纽约做过实习记者。海尔曼玩音乐,中学毕业后就随着乐队到处跑,后来还嫁给了这个乐队的歌手,之后又离婚。迷惘,没有明确的目标,在这种迷失方向的情况下,她开始了写作。1997年,,专心创作一年,完成短篇小说集《夏屋,以后》。该书1998年出版后获广泛好评,作者因此获不来梅市文学提携奖、胡戈-巴尔奖、鲁道夫-亚历山大基金会奖、克莱斯特奖。
关于《夏屋,以后》,整本书的色调正如作者海尔曼的照片给人的感觉:冰冷中隐隐透着温柔。这些故事情节并不曲折离奇,节奏也悠悠缓缓,但海尔曼丰富的想象力、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把握随处可见。
《飓风》中,发达社会中的女青年来到古风尚存的海岛上度假,结识了一位已有家室的当地男子。岛上有原则、有限制的交际作风让女子大为不快,而女子的风流轻佻、若即若离又让男子倍受煎熬。女子最终在飓风到来之前回到自己所在的城市,继续轻松惬意的生活,留在岛上的人们却要面对飓风和女子离去后的残局。
《洪特尔-汤普森-音乐》一篇中,年轻女子由于巴赫的音乐闯进了一位行将就木的老头的生活。女子约老头吃饭,老头如临大敌,忐忑许久之后忍痛割爱为女子准备了一份珍贵的复活节礼物。然而老头的举动再一次受到了女子自由随意的性格的嘲弄。
在《在奥德河的这一边》中,老人充满田园诗意的家庭生活被朋友女儿的不请自来打破,老头对年轻一代的作风颇为不乐却无可奈何。
有人这样评价:尤迪特·海尔曼的作品主题始终围绕着爱情和事物的暂时性,围绕着对尚未体验过的生活、对遭受挫折的生活的恐惧。不确定、不可名状的渴求和欲望;迷惘、彷徨、无望、忧伤……这一切看似虚无缥缈,实则刻骨铭心的情感描述构成了全书的基调。尤迪特·海尔曼表达出了一代人的生活感受,波动了一代人的心弦。冷静的笔触背后,是悲哀而无奈的目光。海尔曼善于将庸常乏味和徒劳无谓化为诗,化为艺术,传递出来自失意世界的信息。她的人物体现了未得到回应的细腻情感的特殊瞬间。
我们重点说说《马尔特》吧,这个发在大益文学的第五期《跃》的“对垒”栏目上的短篇。《马尔特》选自尤迪特·海尔曼曾获得荷尔德林文学奖的第三部小说集《爱丽丝》。2003年,海尔曼的一个作家朋友邀请她去意大利加尔达湖的居所拜访,当她到达的时候,朋友却突然去世,这次经历让海尔曼有了创作《爱丽丝》的冲动。《爱丽丝》一共包括五个短篇,分别以五个死去的男人命名,马尔特是其中第四个男人。这些故事里,都贯穿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性人物爱丽丝。
说回《马尔特》一篇。马尔特是爱丽丝的叔叔,他们从未谋面。在爱丽丝出生前的三个月,马尔特了。马尔特是同性恋,他的死亡成为家族的隐秘和禁忌,家人们怀念他,但又极少谈论他。关于他的死亡,所有人都语焉不详,爱丽丝很困惑。于是她找到了马尔特当年的同性恋人弗雷德里克,希望从弗雷德里克那里得到些什么。弗雷德里克,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和爱丽丝在酒店旁边的河边走了走,一起喝了茶,最后交给爱丽丝一个小型文件夹,里面是他保存多年的与马尔特的通信。
整个故事大致就是这样,然而整篇小说写的又不止这些。《爱丽丝》的节奏非常迟缓,甚至可以说没有速度,整篇小说就像一幅静物油画。我们刚才理出来的故事梗概,在小说中是以能见度非常低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小说中大量的笔墨其实是关于细节,是一处接一处细节的描摹和呈现。
这也就难怪这篇小说会没有速度。
阅读这篇小说,就像是驾车在雾中行驶,前方模糊,后方朦胧,后不见来路,前不见归途。能见度一米的范围之内,倒是可以清晰的看见公路旁边的草,露水和树叶。你小心翼翼,阅读的速度只能屈从与作者叙述的速度,你感觉全身的血液在慢慢淤塞,慢慢停止流动,大脑中却有一条脉络在越来越清晰。当你终于走出浓雾,合上书本,深吸一口气,血液开始重新流淌,脊梁骨一阵一阵发凉,头脑中的脉络清晰为路径,整个故事以一种水落石出的姿态站在你面前,旁边是你在浓雾中见过的印象深刻的草,露水和树叶。
这就是细节的魅力。这篇小说的细节,那些事无巨细、层层堆砌的细节,已经成为整篇小说的神经末梢、毛细血管和触角,它为故事提供了该有的不该有的一切角度、深度和维度,它给读者带来了情感上的亲近和共鸣。这么说吧,这些细节最后堆积出来的,是生活,是广阔的、真实的、会被读者认可和接受的生活。
比如,在小说里,海尔曼写爱丽丝看到:“在一家咖啡店窗外,一个女人脱掉了毛衣,但她的辫子在衣领处给绊住了——毛衣里是一件褪色的粉红色衬衫——她的腿还盘绕在高脚凳的支架上。在一座建筑大门外,一个工人关停了混泥土搅拌机的滚筒,然后摘掉手套。在一辆停靠在路边的出租车内,司机在睡觉,他的脑袋低垂在胸前。”这段话对故事的推动和发展有什么作用吗?没有;对小说的主题有揭示和提升吗?也没有。这段话,包括小说中其他类似的细节,它们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对生活的描摹和塑造。
我们不管在哪里都能看到把车停在路边等人,自己抽空眯几分钟的司机;德国也好,中国也罢,到处都有穿粉红色衬衫的女人;不单单是在德国,我们中国的街边,我们中国的咖啡馆窗外,也会有女人把脚盘在高脚凳支架上坐着。这就是生活,真实的生活。它是德国的,但是中国读者看来,也不会有代沟,不会有隔阂。
优秀的作品都要做到这一步,要把生活呈现出来,然后在这些生活细节里,让读者心头一暖会心一笑,或者是找准地方直接给读者致命一击。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五六年前读奥尔罕·帕慕克的《雪》,里面写到伊斯坦布尔的男人们抽烟,把烟灰弹在吃掉果肉的橘子空壳里,我当时会心一笑,因为我爸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也这样干。所以,直到今天,我看到有谁随意地把烟灰弹在橘子壳里,我就会马上想起奥尔罕·帕慕克和他的《雪》。
我想,如果以后我在街边的咖啡馆外,看到一个把腿缠在高脚凳支架上的女人,我会马上想起尤迪特·海尔曼和她的《马尔特》。每想到一次,我就会惊讶一次,我会惊讶于尤迪特·海尔曼,竟然能在一个短篇里,做到对生活如此精准的呈现。我会惊讶,我会感叹,这个今年已经48岁的德国女作家,从《夏屋,以后》到《爱丽丝》,一点一点写下德国人的生活,写下如此广阔又真实的生活。她是在用细节,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德国。
尤迪特·海尔曼笔下的世界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到就像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真实到像他的偶像契诃夫。我想,在华语世界里,应该还没有那个作家做到这一步。看过海尔曼之后你会觉得,之前以细腻著称的华语女作家,还是都太粗糙了。
当一个德语世界的作家,不管不顾,不理会历史,不理会民族,轻装上阵,写下自己独特的文字,让这些文字在世界范围内激荡出声响。我不禁会想,同样背负着沉重历史的中国作家,他们到底何去何从?海尔曼的写作会对他们有启发作用吗?不知道。不管怎样,像海尔曼一样生活,像海尔曼一样敏感细腻地观察,最后回归到人,回归到生活本身,总是对的吧?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欢迎分享到朋友圈✬
评论功能现已开启,我们接受一切形式的吐槽和赞美☺
大益文学
文学 | 品位 | 经典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taeteawenxueyuan”添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