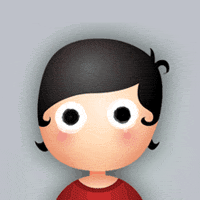假装为鲍勃·迪伦的获奖鼓掌,你其实蓝瘦香菇——为至(装)纯主义者拟写的问答
鲍勃·迪伦,摇滚和民谣歌手,居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点草率的样子,这一次评委可没有打盹。一两个人这么说,很多人就跟着说了。你当然不想落下,不然显得有点LOW。
可怎么定位这个人呢?诗人还是歌手,抑或其他?哦,你忙不迭地在公号上大谈他的”诗“,“不要告诉我你没有读过鲍勃·迪伦的诗”“迪伦说:我首先是个诗人,然后才是歌手”,云云。不要骗我,你真的发自内心地认同迪伦?他的“诗”在你的观念中,和你严防死守的那一类“诗”相安无事吗?不要蒙我,即便你假惺惺地“赞赏”他,为了显示自己开放的诗歌观念,你真的找对了谈论迪伦的方式吗?
你是一个诗人,和他们一道,始终在纯洁的诗歌园子里辛勤耕作,心无旁骛,不无ku(苦)bi(逼)地写着当代的中国诗歌。对了,你也有可能只做点诗歌批评,为衡估何谓“诗性”殚精竭虑。可是,你一下子露出了马脚,因为你竟然用过分简洁的“打破雅俗边界”这种空洞的说法瞒天过海;最要紧的是,你理所当然地把你和更多中国诗人的诗作为完成了的杰构,而把迪伦写在纸上的——喏,那些以诗之名的翻译不断冒泡了——”词“视为完成物。哈,你暗自惊叫起来:“我的天,洒家的诗在审美性上并不比迪伦弱耶!明年,要不后年吧,花落我家了。”
没错,这就是你的逻辑,把自己完成了的、封闭的作品当作标准,以为迪伦的也是完成物,把他偷偷地、信心百倍地踩下去。我得说,你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注意到、没法说清楚迪伦的词(诗)只是“诗”的起点,站在终点的人怎么比得过站在起点的人呢?你不知道他会飞到哪儿。这是一种未定性。你无法想象他何时、何地如永动机般地破坏、反抗一下子,而你早早地坐在终点自摸,顾影自怜。
你应该逐渐明白过来了。我的意思是,你若不改弦更张,只能继续蓝瘦,继续香菇。可你在心里较劲,被那么多诗人,叶芝、艾略特、米沃什、希尼反复经营的诗的审美体系肿么啦?崩溃啦?民谣的、吟唱的、嚎叫的东东怎能登大雅之堂?
多年来你不管懂或不懂,已深深陷落在所谓精深的象征和表现系统中,不能自拔地“纯洁”着我们的语言,撵着“诗性”的屁股汗流浃背,任劳却经常不能任怨。我知道,你要争辩:“我维护着纯洁性,再努力地‘介入’这个时代。我超级激进,关注底层,经常临界着诗哲郭沫若所说的状态——‘我的我要爆了’呢!“当然,你可能属于忠厚老实有良知的那一个,不像一些玩弄修辞策略的人,把体面的现实从开端倒腾到结尾,在闪烁其词中变得更体面。你不知道的是,哪怕你”胸中的道德律“如闪闪红星,你在具体操作上也高度信任着”审美地介入“,可你介入了啥子?你的苦大仇深也许一点不假,并狠狠踩下了审美的引擎,更是超越了小我的种种不堪,那又揭示了什么?因而,我不愿致敬你,顶多只致以克制的同情。
这时你鬼使神差地念叨起了查良铮蜀黍翻译的叶芝:”是变了,彻底地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不过,你其实仍不明就里。
你到底错在哪儿?两个地方:第一,你心中有一个神,一个形而上学,守在一个被庞德艾略特们的某些养分充分抚育的系统,你拼命做着他们忠诚的、发扬光大的徒子徒孙;第二,你把鲍勃·迪伦抽离了鲍勃·迪伦,把他写在纸上的词(诗)和你自己的、在这个伟岸传统中的诗比了一下,趁四下里没人,愤怒起来——这是诗吗(我想起姜文在电影《寻枪》中,当小偷手中的”枪“打到他的要害部位时的抓狂:”咋会是假枪咧“),然后感伤起来,感伤于无地。
电影《寻枪》片段
根本上,你以所谓的诗本体要求诗,戴着本体的眼镜审察迪伦,你才瞠目结舌。先锋的小说家北村如此感叹:
采自腾讯新闻《鲍勃·迪伦获奖引争议,中国作家怎么看?》
可是呀,我忍不住要泼你冷水:本体论是诗的难以察觉的,被百般骄纵的”业障“,在无中心的时代(你以为还有中心,不由分说地认准那个神,却在不知不觉中帮忙巩固着那个本应让你倒吸一口凉气的神的镜像),你不由自主地树立起一个至为纯洁的”诗“标杆,并不无狡黠地时时把标杆变成抽打他人的鞭子。
你可能仍旧不太明白。接下来,我只好啰嗦点、具体些地和你八一八:第一,为什么不能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地以我们的诗和印在纸上的供人阅读的迪伦的”诗“相提并论?实际的情形是,迪伦站在”起点“的”词“赢得了未来,而你躺在”终点“睡大觉。第二,为什么迪伦用站在”起点“的”词“(持续地)打开着世界,用诗的”外部“重新塑造了”诗“,而这种”诗“你和很多诗人却没能写出来?这和是否吸过毒无关。根子里,你妄想用内部决定”外部“,用假装的纯洁掩耳盗铃。你不但没有听见”世界那么乱,装纯给谁看“的当头棒喝,更重要的是,你没能想到,环境中的艺术有意地用种种不洁拯救了虚假的纯洁——值得铭记,艺术家的迪伦大于诗人的迪伦。
迪伦让”诗“站在起点,而你让诗睡在终点
先要说说你的自以为是。你一看到貌似随性、充满毛刺的文本,就惯于觉得它们不够纯,不够装。可是,你怎能以最一般的修辞学来审视迪伦的词(诗)呢?他的”技法“确实显得浅陋,他哪有叶芝、艾略特的心情?后者以完成性的动作锻造他们的”象征“和客观关联物,后者(那是盛现代主义及其余波流溢的年头)大部分时刻都得正襟危坐地,将词放到砧板上反复捶打,以便抽细坚韧的语言之丝,捆紧”物“的脖子。他们几乎没有学会举重若轻,这与时势与脾性与他们惟一的媒介(语言)不合。
请注意,迪伦只要草稿,这只是、仅仅是他后来(反复)表演的起点。你,以及更多的人,怎么好意思以自己的艾略特式的终点去比人家的起点?这好比指定迪伦只能用他庞大武库中的一件,而你押上了全部家当的大炮。这不公平。你确实是这么干的,对着写在纸上的词心里暗笑:”这个我也能搞,而且搞得更好。“
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不幸地、错误地把作为词的文本孤立出来PK,得意洋洋:这个纸上的东西是彭斯的歌谣式写法,你我其实都对彭斯的“我的爱人是朵红红的玫瑰”烂熟于胸。胡适之的朋友刘半农早在1920年代也有《教我如何不想她》:
你可能没有细想过,赵元任将它谱曲之后传唱的情形。譬如我吧,当然也包括你,如果想象自己是个赶脚的旅人,《教我如何不想她》适合在落霞满天的时刻,淡淡地忧伤一下子。
你终究没能意识到,《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调子为固定的伤感格式打造,这种袭自古典的因物起兴,拿来唱也没用。一唱三叹的格式如此霸道,以致只能拿来伤怀。
你还是不死心,讥讽着迪伦的”飘“。但是,你真的应该明白,迪伦的词(诗)不过构成他作为整个表现的摇滚的底本,是出发点,而你用站在终点的”诗“封闭它们。这让我也有点伤感了。于是,只有继续八下去,扯一扯迪伦不只把风中”飘“的答案刻在“飘”的确定与不确定之中,而且,他”飘“成了滚石,而你却梦想着成为钻石。
迪伦让”飘“成为”滚石“,而你总想成为钻石
为什么你会这样,如此天真地以为迪伦的”词“太天真了?因为你没有认真思虑迪伦如此”飘“、如此随便的”诗“的句法结构意欲何为。你本来是很在行的。现代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扭断或者重造句法的脖子。只是,你成为狠角色之后,过分崇拜着句法,以致分出了好的、高逼格的句法和差的、LOW的句法,仿佛前一种句法能包打天下。不知你想过没有?除了外部的高压、残暴构成着压抑的体制,你的内部,所谓的”美学“也是体制,你和不少人误解了康德式的”自律“,仿佛天才是自主的,是自我决定,大家拉出来遛遛,比小聪明,比禀赋。
可惜你错了,而且大错特错。我得郑重提醒你,倒是句法极有可能在自我决定着,你给它戴上形而上学的帽子,它就得意忘形,恨不得自己生产能指不说,还忍不住和外部的——那始终无所不在的控制人的结构相安无事,或眉来眼去,当所有人觉得”安全“,你和你的句法终于被收编了。
相反,迪伦大量的似乎如此容易,没有在你心仪的”陌生化的“感觉器官上引起共鸣的句法,却是为了他的唱,为了他在唱和表演时不断加入即时的、此刻的”感觉“。
你得看真了,被你背地里嗤之以鼻的迪伦的”词“,他的起点,是为了在表演中展开调适或者修正(说他修正,我猜测,为了因应表演的需要,那些词的氛围有时还是太雅、太单一、太有方向性了,他得随时随地地相机形成自己的方向感)。对他而言,表演是搅拌机,是在相应的环境、心境中重制。那些重复、交错的句法恰恰提供给他从起点起跳的自由,这种”飘“,不只”飄“在风中,它是滚石,是惊雷。冷不丁地炸你一下子,冷不丁地上一次在61号高速公路上炸,这一次在斯德哥尔摩炸,下一次则炸在你的诗歌奖颁奖会现场。滚石一样碾过来、碾过去,。
(《像一块滚石》原文,我不太敢像你那样用”原诗“)
你要怪我说得飘,说得太比喻化了,那就说得实(石)一点。这些看上去LOW的句法结构,是为了反抗修辞和美学的捆缚,所以经常随意地游来荡去,忽而素面朝天,忽而蓬头垢面。说到底,是为了迎纳外部的反抗。迪伦一定觉得,那些看似不LOW的奇装异服下的修辞,本质上却循规蹈矩,正在用一种结构对应另一种结构。对应得越好,那些权势的笑脸就越狰狞。所以,我大体同意陈晓明关于迪伦的”异质性“的判断(他还有关于获奖是”评委们的行为艺术“的评价,实际是次要的、随性的表述,可参阅全文),可以补充的是,这种”异质性“或者非同一性挨着那些看似肤浅的句法结构,它们互为因果,”异质性“不断生发的同时,句法结构也在特定的表演中转向、移位和重设,这是进行时的艺术!看哪,那双虎视眈眈的规制之手已经束手而无策了。
采自腾讯新闻《独家连线北大教授陈晓明:鲍勃·迪伦获奖,是评委们的行为艺术》
呀,扯来扯去是希望你明白,迪伦从一个被你看扁的表面上比较低的起点出发,、破坏的方式重建了我们幻觉中完好,但已轰然倒塌的艺术伸展下去的理由和可能。你极有可能不喜欢听到如下沉痛的告诫:如果你不从实践和观念上尽可能地改弦易辙,迪伦将是始终困扰你的显见的”起点“,这将成为你切肤之痛的”梦魇“,因为固守所谓的诗性(文学性)再也没有理由成为形而上学了。
可是,你没法模仿鲍勃·迪伦,因为你不太可能去搞摇滚,但约略可以学到的是,延迟你的”文本“的终点,或者想办法拆开密闭的文学城邦的某个墙角,让旷野的风透进来。这么说着,我实际也有一些伤感:根本上我们无法用现有的、既定的”诗“内涵来谈迪伦的”诗“,因为迪伦以表演的进行时始终在改变着”诗“。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诗(文学)的内城危机。它不是一般的危机,而是,在诗(文学)的疆域之内诗(文学)不再成为可能。我愿意和你一起认真地打量,那些最忠诚的诗人(作家)正决绝地、一往无前地深入,使劲地臆想着、实践着用纯粹的刀锋切入现实之痛。然而,即便这算不上绝对的天真,也过于偏执了,毕竟,定点的那个”刃“难保不被磨损,难保不捉襟见肘,而人们尚无法像迪伦那样的办法——假以进行中的动作,如此说来,诗(文学)大概已经抵达了它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