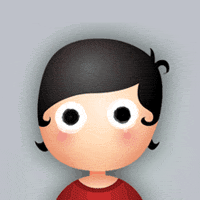张晓舟:明天,放他们自由
文 | 张晓舟
一位爵士乐手在评论第三届明天音乐节李剑鸿、马木尔、张东的专场演出时,怒斥李剑鸿“所作所为与音乐无关”。而这句话恐怕多少反证了明天音乐节的宗旨及其成功,所谓“所作所为与音乐无关”,恰恰意味着拓宽、打破音乐的疆界,深入更为暧昧复杂的艺术与社会腹地。明天音乐节是罕见的足以引发众多外地乐手和音乐工作者前去观摩学习的音乐节(连英国著名前卫音乐杂志《WIRE》的主编也自费前来),更可贵的是,它能引发音乐及社会文化的热议和争鸣(而巨无霸的草莓音乐节引发的争议,似乎主要是在受众服务方面,而很少与音乐本身有关)。
明天音乐节举办之际,恰逢中国摇滚三十年纪念日,可惜这种纪念只是再一次沦为一缸子娱乐口水,既缺乏历史研究的厚度,也缺乏迫切尖锐的问题意识。
一个富于前瞻性的音乐节理应提出各种尖锐的问题,激发不同场域的连锁反应。
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摇滚三十年的提问时我说:假如非要有什么纪念,最好的纪念就是现在进行时的音乐行动,比如明天音乐节,比如木推瓜乐队的复出。
明天音乐节容易被误解为一个纯粹的前卫音乐或实验音乐聚会,但事实上摇滚乐始终还是占有相当分量。假如说第二届的“锈”(哈萨克语TAT,马木尔和张东的一支新乐队)还稍具前卫色彩,那么第一届的舌头乐队和第三届的木推瓜乐队,可能在音乐上并不见得多有明天音乐节特别提倡的“前瞻性”。这两支从中国摇滚乐世纪之交那个不为大众所知的地下年代卷土重来的老牌乐队,。
张楚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提及:中国摇滚的核心就是反抗,言下之意是他要打破这种狭隘的认知。张楚自己的作品无疑很好地打破了这种狭隘的认知,但是他的这一观点表达却是二元对立的、似是而非的,同样是狭隘的,在明天音乐节面前,,更不用说,“中国摇滚的核心就是反抗”这个判断简直是对中国摇滚离题万里的抬举。“中国摇滚的反抗”——这当然堪称一个宏大的命题,但当摇滚乐逐渐汇入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潮流,这一命题早已不断被稀释。
木推瓜十五年来的第一个现场令人兴奋,但也有一位朋友略表失望,他指出:木推瓜的东西还是太老了,曲子太长了。这确实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尽管宋雨喆完全具备偶像派的实力和颜值,但这支乐队有点不合时宜。木推瓜堪称“打口时代”的恐龙,从他们的音乐你能听到九十年代“打口文化”留下的美学烙印:从艺术摇滚前进摇滚到GRUNGE,从布鲁斯硬摇滚到朋克。他们又是中国当代历史的摇滚游击队,假如中国摇滚的核心真的就是反抗,那木推瓜就是那个燃烧的地下祭司,但他们又有中国早期摇滚前辈所缺乏的反讽精神,有异于早期中国摇滚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木推瓜是完全现代主义的,他们是悲剧的废墟上,一阵阵凄厉的狂笑。
当中国摇滚三十年呼啸而来,木推瓜就像一节脱轨的车厢,将一场怀旧的纪念提升为残酷的祭奠。,忽略了其歌词承载的思想表达。
木推瓜的《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哆嗦哆》、《鸟人》、《悲剧的诞生》等旧作(即将结集为专辑《悲剧的诞生》于6月24日在北京愚公移山首发)依旧精准击中这个“小粉红+小确幸”的新时代。而《穷魂》等新作不像他们很多旧作那样在节拍和结构上刻意追求巧思和怪癖,而显得更为直接坦荡,迎面对“新时代”来一次朋克爆破。假如三十年来我们面对的巨无霸社会机器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那么不合时宜就意味着对时代屡败屡战的突围,木推瓜来得正是时候,既不怀旧,也不面向未来,他们就是此时此刻的中国,破碎的镜子,晕眩的风景。
▲ 木推瓜乐队在演出(摄影:子弹)
噪音无疑是明天音乐节题中应有之义,尽管这个音乐节时常被误解为所谓“实验噪音”音乐节。假如“自由即兴”更多的与爵士乐而不是吉他和硬件效果器噪音联系在一起,恐怕就不会触怒学院派——类似的针对噪音的批评层出不穷,但那位可敬的爵士乐手义正词严的短文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其颇具“噪音不适症候群”的典型症状,作者指控李剑鸿“永久性损伤在场所有人听觉系统”,令人眼前浮现出几百号人捂着双耳纷纷倒下并接受爵士大夫紧急治疗的末日图景,但过度发达的形象思维,显然妨碍了对貌似抽象的音乐的感知,作者用“骏马奔腾”和“结实的馕”这样的语言去形容他心目中两位新疆乐手(马木尔和张东)应有的样子,而他对音乐的想象力当然超过对新疆的想象力,于是又将李剑鸿视为“西红柿蛋花汤上的那层油花”。
尽管李剑鸿马木尔张东的演出的得失值得探讨,但一个用小提琴高频来衡量吉他高频的论者和你实在不处在一个频道频率。吉他高频损伤听觉系统,而贝斯低频则烧坏了低频音箱,因此在最后的八人自由大即兴之后,faUSt(浮士德)乐队的JHP(Jean Herve Peron)和马木尔互相交换贝斯弦留念。
▲ faUSt乐队(摄影:子弹)
尽管鸡同鸭讲,但这场小小的争鸣有助于稍微澄清一下对于前卫实验音乐的评价方式。比如说,“对”和“错”在这里是暧昧含混的,甚至是可以被随时颠覆的。既然是“实验”,就意味着冒险和试错;另外,正统观念中的“错”,恰恰往往是前卫实验的“对”。本届明天音乐节还有一个有趣的讲座:《效果器革命美学:声波毁灭者的诞生》,主讲人是纽约的效果器发明家和制造商Oliver Ackermann。马木尔在国外网站上买他的产品,并将之推荐给明天音乐节(马木尔也趁机买下了这次Oliver带来的大部分自制效果器)。Oliver Ackermann演示了如何发现意外,利用错误,制造事故,从而获得形形色色的噪音声效,错误本身,就这样被提升为美学和形而上学。
本届明天音乐节的焦点是faUSt,灰野敬二当然也够吸引,但毕竟他来过中国好几次了,而在中国看到faUSt的现场,这是比较难以想象的事,因为他们在欧洲也很少演出。1994年faUSt曾邀请了灰野敬二充当美国巡演的嘉宾,而这次他们又旧梦重温,在深圳会合。
▲ 灰野敬二(摄影:乐与饵)
faUSt对Kraurock给出过自己的解释,或许这才是Kraurock的最好定义,他们指出:“Kraurock这个名字本身是反讽的,因为我们既不摇滚也不德国,而是站在对立面。”这是对英美主流摇滚的反讽,也是对民族国家身份标签的戏弄。当然,也可以将之视为一种“反摇滚的摇滚”,faUSt为摇滚乐注入了前卫实验的思维和想象力。唯有亲睹亲聆Zappi大爷的鼓,才知道那味道没法仅仅用“复古”来形容,只能说是一种特别的“泡菜Groove”,那节奏和音色就如同他的鼻子一样奇趣盎然。faUSt的迷人还在于其貌似“所作所为与音乐无关”的当代艺术与文学视野,与其说是所谓“跨界艺术”,还不如说faUSt的现场就是一部前卫艺术史绵延不绝的回声:达达主义、激浪派、博伊斯、偶发艺术、即兴诗歌……至于液化气瓶和水泥搅拌机车,则早就成为其“工业现成品乐器”。
▲ faUSt演出现场(摄影:ranzzi)
▲ faUSt演出现场,右后方为道具水泥搅拌机(图源网络)
faUSt还故伎重演,打算像在欧洲一次巡演那样,带上德国毛线请几位女人在台上打毛线。没料到这一次三位中国毛线女即兴发挥,在艺术家魏籽(她也是本届明天音乐节的视觉设计师)的设计下,打毛线不仅仅是舞台视觉行为戏码,而变成了另一件开放的自由生长的作品:魏籽、Tina、亭亭三个人戴上了面具,不是分头打毛线,而是三个人同时合力织造,并改用更粗的毛线去织一块更大体量的织物——粗线条和大体量更符合这场演出的风格,三人还根据音乐的节奏去打毛线,并且一曲结束后立马另起线路,令这块织物始终处在难以名状的未知和未完成状态,她们在最后还放下毛线,改啃瓜子——一个中国经典日常行为。魏籽在演出后,用颜料沾染现场留下的瓜子皮、小石子(在水泥搅拌机搅拌过,并且被Jean Herve Peron倾倒在自己身上的石子),以及供前面观众坐垫的地毡碎块,将之即兴扔到一块儿,并跟面具和织物一起拼贴构成了一件作品,而这件作品也将成为faUSt的唱片封面。于是,faUSt的中国现场不仅仅是有了“中国元素”,还制造了新的扩张和循环。
▲ faUSt现场的中国毛线女(肖蔚鸿摄影)
▲ FaUSt现场拼贴作品(摄影:魏籽)
与其翌日的个人演出相比,灰野敬二作为faUSt的嘉宾乐手的表现同样令人折服,多一分太多,少一分太少,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自由即兴的化境。最后他还充当了faUSt、Oliver Ackermann,以及李剑鸿马木尔张东的八人即兴的指挥——或者不如说是开关——潇洒操控这一场自由即兴的大戏。无法用绝对化的概念范畴去看待灰野敬二,前卫应该逃避情感?灰野并不乏抒情的时刻。实验就应该节制情绪?灰野用沛然莫之能御的情绪去传染乐器和效果器——以及:声音和空气。这是情感、情绪、能量、肉身(动作),与声音的合一,或许唯有以“气”名之,有和无、虚与实、铺张与空白、灿烂与幽玄、前卫与传统一气贯通,当灰野最后祭出其独门法器——密集拉伸的钢丝圈——来回跳荡,这充满仪式感的现场令人联想到恐山的亡魂和神巫。灰野敬二不是耍酷也不是灵修,而是最大限度地涤除了情感和欲望的杂质,如果说faUSt的现场充满了由摇滚乐而向现代艺术无限挺进的扩张欲,则灰野敬二在张牙舞爪的暗黑外表下,潜藏一颗俾睨群雄而独对天地的孤独之心。
▲ 自由即兴超级天团(摄影:张晓舟)
▲ 马木尔、张东、李剑鸿(摄影:Sky)
策划人涂飞对民族音乐和对前卫音乐一样热爱,这令明天音乐节总会有一出传统戏码,去年有南音蔡雅艺,今年则来了北印度的西塔琴和塔布拉:Pandit Narendra Mishra与Kushal Krishna。尽管他们热闹的现场赢得了喝彩,但却引发了前卫乐迷的一些负面评价。他们在北印度演出,都是传统风格,不会改编成短曲子,也不会玩互动,乃北印度RAGA的最新优秀传人,但当印度人告诉涂飞“我们给中国观众准备了特别节目”时,却遭到了谢绝,“就演你们自己的,不用考虑我们”。我不知道印度朋友原本准备的特别节目是不是某首改编的中国曲子(例如《茉莉花》这“同一首歌”),但“就演你们自己的”是不可能的——他们当然不可能按照北印度的RAGA套路去国外演出,万里迢迢去演一个小时,顶多只能是去做一次印度RAGA音乐的ABC示范表演。这是全球化必然带来的传统文化的娱乐化和观光化,对于完全不了解印度文化的观众来说,他们更多的只是起到某种“文化使者”的作用。涂飞说他给印度乐手的表演打75分,但我指出:打分的标准乃至打分的行为本身,都是成问题的。一位朋友打断了我和涂飞的讨论:“不要再为这两位印度人浪费时间了,不值得为他们破坏这个美好的夜晚。”
▲ Pandit Narendra Mishra & Kushal Krishna(摄影:一个猪蹄)
然而,这位朋友为这个美好的音乐节提供了一个意外论题:为什么印度西塔琴和塔布拉的优秀艺人会在这里被视为失败甚至多余?对这一问题的解析将明天音乐节从美学引向了文化研究:其一,显然是因为中国乐迷对印度音乐和印度文化的陌生;其二则是对Artist的身份认知差异,Artist到底是艺术家还是艺人?灰野敬二的洁癖和神秘感似乎才是艺术家风范,而二位印度哥们似乎不过是江湖杂耍艺人,他们缺乏节制的炫技看起来像街头杂耍——脖子上盘旋一条大蛇也毫无违和感;其三涉及现场与观众的互动娱乐。但去年蔡雅艺也教观众跟着她一一用南音念诵唱词,有问题吗?为何换成印度乐手要观众与其做节奏互动,就被批评过于取悦观众?为何没人批评faUSt?——Zappi要求观众和他一起根据大屏幕放出来的图形即兴“看图发声”。Oliver Ackermann则把吉他交给观众去即兴制造噪音,为何没人批评他取悦观众?批评者显然使用了双重标准,多少是以西方的精英艺术等级观念,去评判印度古典(传统)音乐的世俗化大众化,同时又以貌似捍卫传统的立场,去评判早已经历现代性洗礼的印度传统音乐。
多年前,塔布拉大师Zakir Hussain来上海演出,涂飞和我在演出前一天曾去聆听一个小型的记者群访会,在场记者显然大多对Zakir Hussain一无所知,甚至有记者要求他先介绍塔布拉鼓。群访结束后我们问了一两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你如何看待伍德斯托克,如何看待摇滚乐文化?”一位老兄后来在网上跳出来抨击,意思是我太不专业了只知道摇滚乐。他似乎没兴趣听Zakir Hussain的回答,而自以为是地拿印度音乐去对抗摇滚乐,但我怀疑他是否知道一个基本史实:Zakir Hussain 的父亲Ustad Allah Rakha 和Ravi Shankar一起参加了伍德斯托克,而伍德斯托克也成为Zakir Hussain的一大文化启蒙。没有美国六十年代以摇滚乐为先导的反文化和亚文化,塔布拉不会成为嬉皮士差不多人手一个的东方风情标配玩具,Ravi Shankar也不会一炮而红,印度音乐文化(和宗教文化一起)也不会风靡西方,中国乐迷也就没法借印度音乐来摆谱。更重要的是,没有Ravi Shankar打破印度传统音乐长篇格式、采用迁就西方受众的曲目结构与命名方式,印度传统音乐也难以在西方传播流行,在六十年代,现代性在印度也意味着时间意识的割裂与重组。尽管流派风格有异,但明天音乐节上的Pandit Narendra Mishra与Kushal Krishna只不过秉承了那个西方镜像下的印度音乐“新传统”,他们在取悦中国观众的同时,不意中也挑战了某种固化的精英优越感。
极少有哪个中国音乐节会像明天音乐节这样令人依依不舍,而又充满对下一届的期待。faUSt的安可曲,是Peron弹琴伴奏,请中国女孩尹思卜和詹楚玥用中文翻译朗诵他女儿的一首短诗,或许,这也是明天音乐节永恒的献诗——
我们应该存在
或消亡
天使
对皇后说
我提起我的裙角
当伏尔泰
慢慢转身
当我说话时
满嘴蒜味
白色
是的!
白色
我们不幸的命运
他告诉你
成为自由的人
而你遵守了
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吗
一场闻所未闻的战争
或是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街道
在那里 婴儿接二连三地死亡
系统
理论
或是我们的愿望
放他们自由!
分析
组织
批判
分析
组织
批判
直到最后发现
没有人能确信这曾真的发生
【作者简介】
张晓舟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乐评人,音乐策划人和唱片监制。
【精华推荐】
·END·
大家 ∣ 思想流经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见 · 价值 · 美感
※本微信号内容均为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转载将追究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联系ipress@foxmail.com